专家观点
跨境区域化发展对边境安全治理提出新要求
自古以来,边境地区就是中国和周边邻国进行联系与互动的纽带。边境安全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随之而来的跨境区域化发展,推动形成了边境地区的新发展格局,边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境安全,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了边境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和新路径,统筹推进了边境安全治理工作。因此,深入研究新时代边境安全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推进边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跨境区域化发展改变了边境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也对边境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边境地区“开”与“关”的兼顾与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极大促进了中国和周边邻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边境口岸等在过人过货的基础上,也兼具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重任。然而“五通”建设在便捷了边界线两端的“人”和“物”跨境往来的同时,也增加了“三非问题”,以及非法贸易、走私、病原体等问题输入的“便利度”。人员、货物的跨境流动使国民所在地、货物所属权与国家主权行使的地理空间范围发生错位,因此,如何既能维持合法过境、区域合作、贸易往来的正常运行,又可以抵御、防范跨境安全风险,就对边境安全管控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边境安全管控主要是规制性管理边境事务、问题和活动,管控客体包括“人”和“物”两种,管控方式则是对人和物跨境流动的监督和管理。当前,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安全面临着“开”和“关”的兼顾与平衡问题。一方面是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坚持制度型开放,增加“人”和“物”的跨境流动,强调边境地区的“发展”内涵。另一方面则是对“人”和“物”跨境流动的监管,强调边境地区的“安全”内涵。因此,如何平衡边境大门的“开”与“关”,是在跨境区域化发展中建构综合边境安全管理体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例如,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公路、铁路、航运、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加强巡逻公路、巡逻铁路的建设,修建铁丝网、铁栅栏等物理阻拦设施,努力切断跨境违法犯罪团伙实施犯罪的物理路径,并在边境沿线设置检查站、治安卡口,加强对过境人员、货物的检查。而在技术发展方面,一方面,边境地区需要“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口岸的运行管理效率和跨境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程度。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智慧边海防建设,“借助5G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力量,将以往单一的‘人防’或‘技防’的方式转变为人机结合的‘智防’模式”,不断提升边境管控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有效防范边境安全问题的外溢、内渗和联动。未来,随着跨境犯罪活动高科技化水平逐渐提高,有效构建融合监控摄像、无线传感器、无人机、AI、3S、生物信息识别、北斗实时定位等先进技术的智能应用系统,也将成为边境安全管控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二,边境地区“内”、“外”治理因素的协调问题。跨境区域化发展推动边界两侧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使边境安全治理突破国家治理范畴,具备了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意义。很多时候仅依靠一国之力已无法单独解决问题,而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性的区域合作来协同治理内外交织的跨境问题。所以,如何协调“内”、“外”治理因素,建构“内外联合”的协同治理体系,同样是当前边境安全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对于域内治理来说,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应对内外安全威胁与挑战的重要前提。域内治理从根本上依托中央一地方的国家治理体系,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国家需要对边疆发展与安全进行整体性战略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在此基础上,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作为域内治理的主导力量和首要责任主体,则负责边境安全战略谋划、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国防和边防力量部署、边境政策制定、治边资源统筹协调和配置等工作,确保把党中央的治边方略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同时,国家还“通过宣传、国民教育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化手段,强化国家符号体系在边境地区的普遍存在,实现国家力量向边境社会的全域下沉和延伸”。针对边境安全问题的总体安全特点,国家多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角度出发,稳步推进对边境安全的综合性治理。
概言之,边境地区的开放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扩大的进程,中国推动边境地区开放和跨境经济合作繁荣,从本质上追求的是构建一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相邻区域形成关联性更强的利益共同体。“随着多层次跨境关系的蓬勃发展,非国家行为引发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下而上的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使边境安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扁平化和直线式的安全,而变成了更加立体化和交互式的安全,既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解决安全问题,也产生了对主体间关系的治理诉求”。因此,在新发展形势下,边境安全治理需要采取区域化治理模式,典型特征就是“区域国家及组织自主决定本地安全事务,掌握区域治理进程中的制度设计与建设、议程设置与推广以及规范创建与扩散”,并“着重强调区域内行为体的能动性,遵循内因是事物发展关键的原理”。在区域化治理过程中,中国与不同周边国家不断建构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多层次安全合作机制与框架。
(本文节选自《跨境区域化发展与新时代中国边境安全治理》,载于《外交评论》2024年第6期。作者李志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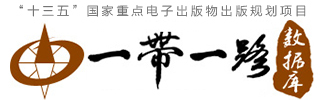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21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212号